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半个世纪后在联大又与美国针锋相对
1998年7月30日下午,北京天气闷热,是雨前的征候,会议厅里却冷气嗖嗖。狭长的大厅摆了两张条桌,上覆白色的台布,显得庄重而整洁。桌边及后排坐了30多名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静候着联合国销毁伊拉克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特别委员会主席巴特勒的到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联合国协会正为访华的客人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座谈会。
巴特勒大使和两名助手准时到达。他是一个高大和壮实的西方人,六十开外,梳着背头,顶发有点稀疏,走在最前面。进场时没有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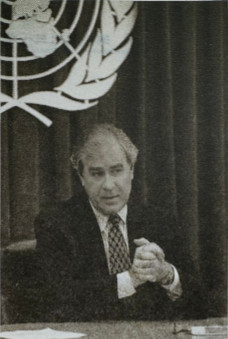
1997-1999年间任联合国特委会主席的巴特勒(图源:《潮头戏水三十年》)
巴特勒静静地在桌子的一头坐下,左右分别是中国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在巴特勒上任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他的强硬态度,几乎酿成两次举世震惊的武装冲突。最后一次危机的“灭火”任务,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同年7月访华前完成的。
会议由中国联合国协会谢启美会长主持。他简单致辞后,巴特勒开始介绍伊拉克特委会的工作情况。他首先表示有幸是第一个访华的特委会主席,此次来华是为了解中国的态度和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交经验丰富。
接着,他用较多的时间解释道,安理会对伊拉克的制裁长达7年,是因为伊拉克采取不合作态度,不提供有关报告和材料,甚至不老实。例如,伊拉克矢口否认有生物武器,现在已开始向特委会提出报告,因而白白浪费了头4年的时间。他还说,中国与特委会过去有着良好的合作,希望这种合作能在今后进一步得到加强。最后,他表示愿意回答在座人士的任何问题。
主宾之间的回答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一位中年学者首先表示,安理会的决议理应得到全面贯彻,但从人道主义出发,他也呼吁加速核查过程,早日解除制裁,使伊拉克人民尽早恢复正常的生活。他的发言无疑代表了在座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巴说他也抱同样愿望,甚至表示一年后他任满时,希望届时伊拉克问题已经解决。但他对伊人民处境困难之说存疑,认为伊拉克并不贫穷,到处是财富,总统官邸附近即大兴土木,何不将钱用来周济百姓?他讲的也许有一定道理,许多国家都存在社会不公、奢侈浪费的现象,但这怎能成为外国施加不公正制裁的理由?

2003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手持样本瓶,向全世界展示所谓伊拉克正在研发化学武器的“铁证”。美国借此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
问:“核查进行得如何?年底可否结束?”
答:“导弹和化学武器已查得差不多,生物武器还刚开始。年底能否结束,一看伊拉克肯否合作,二看大国能否达成共识。”巴特勒先生说话都留有余地。
座谈的后半段,讨论渐入困境,语言逐步加温,同室外35度的高温不相上下。
一名中国专家问:“萨达姆总统已表示,如年底不能结束制裁,将发生严重问题,不知届时会不会发生前两次那样的严重对抗?”
巴特勒说:“球在伊拉克脚下,特委会从不同伊拉克对抗,而是伊拉克对抗特委会。”
接着又有人问:“上次危机时,美国扬言如安理会不采取行动,美国将单干,会不会再打起来?”
这位老练的外交家王顾左右而言他,表示他是搞裁军的,对打仗没有兴趣。

联合国核查人员摧毁伊固定导弹发射装置。
有人问:“特委会坚持搜查总统萨达姆的官邸,结果一无所获,为何特委会给安理会的报告对此只字不提?”
巴特勒先生含糊了一下,然后自我解嘲说:“伊拉克事先已把违禁的武器搬走了。”
这答复实在有点勉强。美国的间谍卫星白天黑夜都在伊拉克上空巡游,如果早知伊拉克玩的是“空城计”,聪明的核查小组还会在国际上大造声势,然后演一出“扑了个空”的戏,贻笑大方?
更有人尖锐地提出,国际上有人认为伊拉克危机背后有美国的影子,问他如何看。
至此,这位澳大利亚前驻联合国大使有点沉不住气了。出于好奇,他反问道:“你是搞什么研究的?怎么你反映的都是伊拉克或阿拉伯人的观点?使用的都是他们的材料?你读过特委会的报告吗?除了他们的报刊,你还读不读别人的东西?”
提问的研究员拟予解释,但巴特勒步步紧逼。两人一来一往、几度交锋,在场的都感到尴尬。
纷争稍平息后,主席宣布提最后一个问题。
一位女士以平缓的口气问:“伊拉克有它的问题,从特委会的工作来讲,是否也有改进的余地?”
巴特勒大使不能说他的工作尽善尽美,只好表示特委会的工作当然要改进,然后提高嗓门,激愤地说:“但如果认为伊拉克问题拖延的责任是在特委会,而不是伊拉克,那是绝对荒唐的!”谁也没有这样认为,是他自己作的结论。
巴特勒虽居客场,却气势汹汹。这场座谈会就以他的咆哮告终?此时,一直保持沉默的我心急如焚,真想说几句话,以多少改变这种态势,但如我发言,必须简短有力、击中要害,使对方无从反驳。我搜肠刮肚,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稍纵即逝。
巴的话音刚落,我就举起手来。但主席已有话在先,最后一个问题已提完,见我举手,便征求巴特勒的意见,可否再回答一个问题。大使先生大概没有想到还有人会打破程序再提问题,便点头同意。
主席提示:“只能是短问题。”
我允诺:“很短。”其实仅有三句话:“1.伊拉克是被告;2.被告应当有权为自己辩护;3.世界是否应当听取被告的意见,以便公正评判?”
巴特勒几乎不假思索,便答:“绝应如此。”
从“绝对荒唐”到“绝应如此”当然是个明显的变化。接着,他用普通语调表示:“特委会在工作中一直注意尊重伊拉克的主权和维护其尊严。 ”
“主权”和“尊严”本是我想说的主题,现由巴特勒本人来说,倒也不错。
特委会的工作遭到联合国内外的广泛批评,更是受到伊拉克当局的坚决抵制。最后,巴特勒未经安理会许可,即将全部核查人员撤出伊拉克,致使特委会名存实亡,巴本人也只好挂冠而去。
1999年12月,安理会设立新的“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观察委员会”取代联合国特委会,但伊拉克一直不予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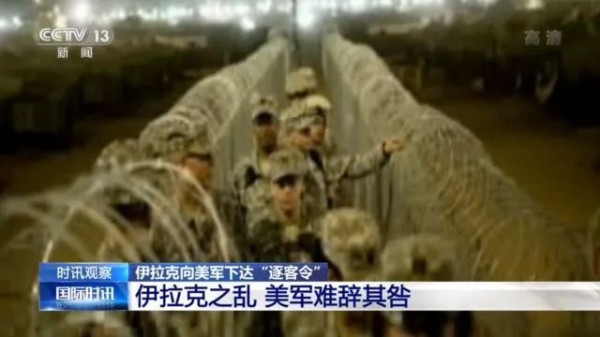
2001年“9·11”之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一年之后,以瑞典人布利克斯为首的联合国监核会又开进伊拉克,恢复武器核查。巴特勒偏袒一方,到处张牙舞爪,在伊拉克问题上虽显赫一时,到头来仍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这是我在国际会议上第二次领教巴特勒了。1990年5月,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召开第46届年会,这位当时被委派为澳大利亚与会代表团团长的资深外交官便在头一天大会上,以“不寻常的直接语言”攻击亚太经社会“效率低下”。这是违反联合国常规的做法。通常有争议的问题都是先在小会上提出,然后再提到大会上讨论。这一突袭引起了许多代表团和新闻界的非议。
醉翁之意不在酒。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他是代表某些国家对亚太经社会酝酿之中的“区域经济合作理事会”作出反应。这个具有较浓的亚太意识的“理事会”不为西方成员国所认可,甚至被看作是同当时刚建立不久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唱对台戏的,而APEC又是澳大利亚的“心肝宝贝”。1989年初,正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克首倡建立APEC的。
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一名熟知巴特勒的驻联合国高级官员发表了对他的评论——“爱挑起事端、美国人的工具”。当时我还不十分理解,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派了大批本国的武器专家在伊拉克全境“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这点上看,巴特勒在职期间这样替美国卖力气,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作者简介

杨冠群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



